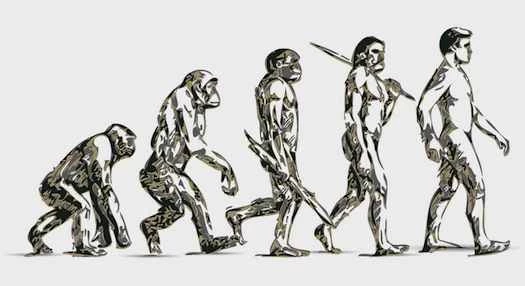
人類的未來會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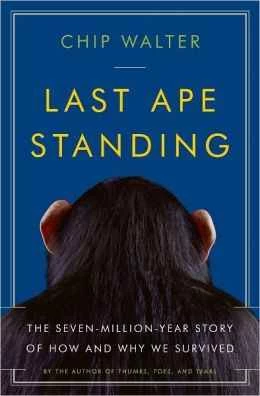
在新書中,奇普·沃爾特分析了現代人類如何進化成如今佔據主導地位且是唯一倖存的人類物種。在此,他展望了人類的下一個篇章。
過去40億年的演化史一再證明,它擁有無窮無盡的變數。只要時間夠長,一切都有可能。自然選擇的力量終將迫使我們分化成不同的版本,就像加拉巴哥群島上的許多雀類一樣……前提是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讓基因來決定我們的進化。
但我們不會。相反,我們將走向滅亡,而且很快就會到來。我們或許是僅存的猿類,但我們也撐不了多久。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想法,但進化的所有機制都表明,當我們成為符號生物——一種能夠將神經元放電轉化為決策、選擇、藝術和發明的動物——的同時,我們也把自己置於了自身的十字路口。因為憑藉這些靈巧而有目的的能力,我們也創造了一種新的進化方式——文化進化,它是由創造力和發明所驅動。由此,一連串擺脫了蛋白質和分子等舊有生物機制束縛的社會、文化和技術飛躍開始了。
我們或許終於遇到了自己的對手:一種連我們自己都無法適應的進化力量。乍一看,你可能會覺得這對我們人類來說是件好事。還有什麼比火和輪子、蒸氣機、汽車、速食、衛星、電腦、手機和機器人更能改善我們的境遇呢?更不用說數學、金錢、藝術和文學了,它們每一項都旨在減輕勞動強度,並提高生活品質。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進步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似乎每實現一個絕妙的新想法,我們就會立刻發現自己需要更新的解決方案,而這些方案似乎只會讓世界變得更複雜。我們如此迅速地掀起變革,製造各種小玩意、武器、污染物以及各種複雜性,以至於作為基因改造適應一個不久前還未經歷過技術和文化繁雜的星球的生物,我們很難跟上時代的步伐,即便我們正是這場扼殺我們自身的變革的推動者。我們不斷創新的後果是,它不可避免地、矛盾地、無可挽回地導致我們創造了一個我們完全不適應的世界。或許,我們最終遇到了自己的對手:一種我們甚至無法適應的進化力量。
我們正在自取滅亡,因為進化的舊有包袱驅使我們這樣做。我們都知道,每一種動物都渴望掌控環境,並且盡力去獲取這種掌控權。我們的DNA要求我們生存。只不過,使我們成為萬能生物、碩果僅存的猿類的幼態持續(青春期)現象,只是放大了而非取代了我們曾經作為動物時的原始本能。恐懼、憤怒以及對即時滿足的渴望依然與我們如影隨形。我懷疑,我們創造力與古老需求的這種結合,很快就會將我們從這片生靈的寶庫中帶走。
我們正被自己一手打造的「美麗新世界」搞得焦頭爛額,而最有力的證據莫過於越來越多的人坦言自己壓力巨大。最近一項研究指出,美國「在壓力和健康方面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 美國人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他們用不健康的方式應對壓力,同時又設置了重重障礙,阻止自己改變行為,從而彌補自身造成的傷害。結果,68%的人口超重,近34%的人肥胖。 (這在狩獵採集社會中很少見。)十分之三的美國人表示自己患有憂鬱症,其中45歲至65歲年齡層的人最為常見。 42%的人表示自己易怒或憤怒,39%的人表示自己緊張或焦慮。 X世代和所謂的千禧世代甚至比他們的嬰兒潮世代父母更容易在人際關係方面感到壓力。情況已經糟糕到連牙醫診所都受到了焦慮的影響。如今,牙醫們花在治療下顎疼痛、牙齦萎縮和牙齒磨損的時間,比三十年前多得多。為什麼?因為我們緊張焦慮,晚上睡覺時磨牙磨得牙齒都快掉光了。
壓力,正如各地實驗室老鼠的經驗反覆證明的那樣,是生物體越來越不適應其所處世界的標誌。正如達爾文和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在150多年前敏銳地觀察到的那樣,當生物體與其環境不再匹配時,總有一些東西會做出犧牲,而犧牲的總是生物體本身。
我們的滅亡或許會像蝴蝶蛻變一樣。
我們是如何應對壓力的?不太理想。研究表明,壓力增大時,我們非但沒有放鬆或增加運動,反而會錯過正餐,花更多時間上網或看電視,然後暴飲暴食,徹夜難眠,以飽滿的眼皮、暴躁的脾氣和疲憊的狀態迎接第二天。是什麼引發了這種行為?正是那些我們竭力想要壓抑的原始本能和慾望。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的滅亡不必是《魔鬼終結者》式的毀滅,讓世界從此空無一人,末日後的城市荒涼破敗,只剩下我們文化成就的殘骸。它或許更像是一場蝴蝶般的蛻變,我們跨越舊我的盧比孔河,蛻變為一個全新的生命,而這一切都建立在我們自身之上,甚至在早期,我們從未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曾經以為的那個物種。第一個尼安德塔人是否知道自己不再是海德堡人?這樣的轉變是漸進的。
或許我們會蛻變為賽博智人*,一種全新的人類,比你我聰明得多,或許更擅長社交,至少能像馬戲團演員一樣游刃有餘地周旋於龐大的朋友圈、熟人和商業夥伴之間。一種更能適應自身所創造的變化的生物。為了應對時間緊迫和遙遠的挑戰,賽博智人甚至可能擁有分身能力,分裂出多個數位版本的自己,每個版本都能各自獨立生活,然後定期重新融合,最終成為一個超大型的個體。想像一下,不像羅伯特·弗羅斯特詩作《未選擇的路》中的旅人那樣,我們可以選擇兩條路,每條路都對應著一個不同的自己。這不禁讓人思考,如果這種可能性真的發生,我們身上某些至關重要的東西是否會消失。但或許,這正是新物種的獨特之處。
一大群智人已經在思考我們未來的型態會是什麼樣子。他們自稱為超人類主義者,期待未來的人類學家回顧我們這個物種時,會認為我們曾經輝煌一時,但最終未能延續到如今的未來。
超人類主義者預言,未來將會出現一種真正意義上半生物半機器的生物。我認為他們的預言是正確的,這是漫長趨勢中合乎邏輯的下一步。畢竟,我們早已與科技密不可分。你上一次查看手機,或像原始狩獵採集者一樣步行上班是什麼時候?我們與工具的共同演化由來已久。只不過,如今人與機器、現實與虛擬、生物與科技之間的界線似乎變得特別模糊,而且很快就會完全消失。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超越自身?超人類主義者預測,將分子大小的奈米機器與傳統的碳基DNA融合,下一代人類不僅可以加速思維、複製自身,還能提升速度、力量和創造力,在探索世界、太陽系乃至最終的銀河系的同時,進行超智能的構思和發明。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許會用人造血紅素取代生物進化經過數億年精心打造的血液。我們或許會用奈米製造的數位神經元取代現有的神經元,找到重塑身體的方法,讓我們永保青春美麗,並徹底消除疾病,讓死亡本身也成為歷史。 「男性」和「女性」這兩個詞甚至可能成為過時的概念。簡而言之,擺脫生物限製或許成為下一代人類的標誌性特徵。
我想,這類改變也可能有弊端。如果我們擁有了近乎超人的力量,卻仍然背負著原始的本能,那該怎麼辦?我們新獲得的能力或許會超出我們的掌控。我們會不會進化成某種漫畫式的英雄和反派,展開史詩般的衝突,並帶來可怕的後果?這樣的力量賦予了「尖端科技」一詞全新的、致命的意義。而那些無法獲得所有這些增強型新技術的人又該怎麼辦?我們是否應該警惕出現一個貧富懸殊的世界?我最關心的正是這些問題。
鑑於進化的軌跡,除非再次發生小行星撞擊或全球性災難,否則我們幾乎肯定會進化成比現在更強大的版本。七百萬年來,這已成為一種趨勢。猿類不斷獲得更高的智力和更多的工具,變得更加智慧,也更加致命。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生存下去……我們自己?我們甚至能夠進化成下一代人類嗎?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我指望我們內心深處的童真能夠拯救我們,那個喜歡漫無目的地遊蕩、玩耍嬉戲、探索未知領域、幻想不可能之事並追問緣由的童真。在轉型過程中,我們不能失去這個不切實際卻又靈活的童真,因為它賦予我們其他動物無法企及的自由——既會犯錯,又靈活多變,充滿創造力。正是這個童真讓我們走到今天。或許它也能幫助下一個人類。
*這個術語是我在上一本書《拇指、腳趾和眼淚:以及其他使我們成為人類的特徵》中創造的。
本文經許可摘自《最後的猿猴:七百萬年來我們如何以及為何倖存下來的故事》。作者奇普·沃爾特是網站AllThingsHuman.net的創辦人。他的個人網站是www.chipwalter.com,他的文章曾刊登於《Slate》、《華爾街日報》、《科學美國人》和《經濟學人》等許多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