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朋友的父親是一位神經外科醫生。小時候,我對神經外科醫師的工作一無所知。多年後,我在麥基爾大學心理學系攻讀研究所時,這個人再次出現在我的生活中。當時我正在閱讀醫學期刊上關於記憶的文章,偶然看到一篇報告,作者是一位醫生,他為一位年輕人做了腦部手術,治癒了他頑固的癲癇。手術導致病人失去了形成新記憶的能力。這篇文章的合著者正是我朋友的父親,威廉‧比徹‧斯科維爾。病人名叫亨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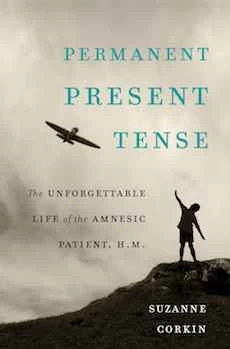
這段童年時期與亨利的神經外科醫生的淵源,使我讀到關於「失憶症患者HM」的文章時更加感同身受。後來,當我加入蒙特婁神經病學研究所布倫達·米爾納的實驗室時,亨利的病例就落到了我手中。 1962年,亨利來到米爾納的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我得以利用這段經歷為我的博士論文撰寫亨利的案例。米爾納是亨利術後第一位對其進行測試的心理學家,她與斯科維爾於1957年發表的論文,詳細描述了亨利的手術及其可怕的後果,徹底改變了記憶科學。
我當時試著透過研究亨利的觸覺(即他的體感系統)來加深對亨利失憶症的科學理解。我對他的最初研究重點突出且時間短暫,僅持續了一周。然而,在我搬到麻省理工學院後,我意識到亨利作為研究對象具有非凡的價值,於是我開始研究他,直到他去世,長達四十六年。自他去世後,我致力於將五十五年的豐富行為數據與我們從他的屍檢大腦中獲得的資訊聯繫起來。
我第一次見到亨利時,他給我講了他早年的生活故事。他口中提到的那些地方,我立刻就能感同身受,彷彿置身於他的生活經驗之中。我的家族好幾代都住在哈特福德地區:我母親曾就讀於亨利的高中,我父親在亨利手術前後居住的街區長大。我出生在哈特福德醫院,亨利做腦部手術的也是這家醫院。我們有著如此多的背景和經歷交織在一起,所以當我問他我們是否以前見過面時,他通常的回答是“是的,高中時見過”,這讓我覺得很有趣。我只能猜測亨利是如何將他的高中經歷與我聯繫起來的。一種可能是,我長得像他當年認識的某個人;另一種可能是,在他多次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參加考試期間,他對我逐漸產生了一種熟悉感,並將這種印象融入了他的高中記憶中。
亨利很有名,但他自己卻不知道。他獨特的身體狀況使他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也引起了公眾的極大興趣。幾十年來,我不斷收到媒體的採訪和拍攝要求。每次我告訴他他有多特別時,他都能短暫地理解我的意思,但卻記不住。
加拿大廣播公司錄製了我們1992年的對話,並將其用於兩檔廣播節目,一檔探討記憶,另一檔探討癲癇。一年前,菲利普·希爾茨為《紐約時報》撰寫了一篇關於亨利的文章,後來又以他為主角創作了《記憶的幽靈》一書。

關於亨利的科學論文和書籍章節層出不窮,他的案例也是神經科學文獻中最常被引用的案例之一。隨便翻開一本心理學入門教材,你都可能在某個地方找到對一位僅被稱為HM的患者的描述,旁邊配有海馬體的示意圖和黑白核磁共振圖像。亨利的殘疾給他和他的家人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但也成就了科學。
亨利如果知道自己的悲劇對科學和醫學做出如此巨大的貢獻,一定會感到無比自豪。在他生前,認識他的人都對他的身分守口如瓶,總是用他的姓名首字母稱呼他。每當我講授亨利對科學的貢獻時,總會有人對他的身分充滿好奇,但直到2008年他過世後,他的名字才為世人所知。
在與亨利共事的幾十年裡,我的使命就是確保人們記得的不僅僅是教科書中簡短而匿名的描述。亨利·莫萊森遠不止一堆測驗分數和腦部影像。他是一位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溫文爾雅且極富幽默感的人,他深知自己記憶力不佳,並坦然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在姓名縮寫背後,是個活生生的人;在數據背後,是個活生生的人生。亨利常常告訴我,他希望對他的病情進行的研究能幫助其他人過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悲劇為科學和醫學帶來如此巨大的益處,他一定會感到無比自豪。

記憶是我們一切行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們往往意識不到它的範圍和重要性。我們常常把記憶視為理所當然。當我們走路、說話、吃飯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的行為源自於我們先前學習和記憶的資訊和技能。我們時時刻刻依賴記憶來度過每一刻、每一天。我們需要記憶才能生存──沒有記憶,我們就不知道如何穿衣服、如何在社區裡辨別方向,或是如何與他人溝通。記憶使我們能夠回顧過去的經歷,從中學習,甚至規劃未來。它為我們提供了從一刻到另一刻、從早晨到傍晚、從一天到另一天、從一年到另一年之間的連續性。
透過亨利的案例,我們獲得了新的見解,使我們能夠將記憶分解成許多具體的過程,並了解背後的腦迴路。我們現在知道,當我們描述昨晚的晚餐吃什麼、背誦一段歐洲歷史、或不看鍵盤打字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調用大腦中儲存的不同類型的記憶。

亨利幫助我們了解喪失資訊儲存能力後會發生什麼事。他保留了手術前的大部分知識,但在術後的日常生活中,他非常依賴周遭人的記憶。他的家人,以及後來的養老院工作人員,都記得亨利當天吃了什麼、需要服用哪些藥物,以及他是否需要洗澡。他的檢查結果、醫療報告和訪談記錄,幫助保存了他無法記住的生活資訊。當然,所有這些資源都無法取代亨利失去的記憶能力。因為記憶的作用遠不止於幫助我們生存──它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質量,並有助於塑造我們的身分認同。
摘自蘇珊娜‧科金 (Suzanne Corkin) 所著《永久現在式:失憶症患者 HM 的難忘人生》(Permanent Present Tense: The Unforgettable Life of the Amnesic Patient, HM),經許可轉載。本書由珀爾修斯圖書集團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旗下基礎圖書出版社 (Basic Books) 出版。版權所有 ©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