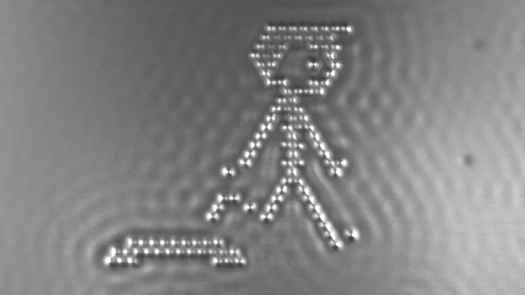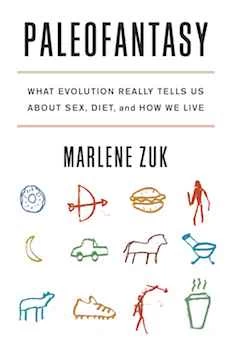
因為我們常常從漫長的歷史長河來思考進化,例如從鰭狀肢到鱗狀爪,再到擁有對生拇指的手,數百萬年來的微小變化,所以我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進化總是需要億萬年的時間。這種假設反過來又讓我們覺得,人類在短短幾千年內就從稀樹草原來到了柏油路,肯定不適應現代生活的快節奏,而實際上,我們或許更適合歷史上那些我們熟悉的生活方式。我們肥胖、體弱,我們患有高血壓,我們還飽受一些我們懷疑祖先從未擔心過的疾病的折磨,例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愛滋病。朱莉·霍蘭德博士在《魅力》雜誌撰文指出,如果你“感覺自己不像個人”,總是壓力重重、精疲力竭,那麼你需要記住,“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違背了我們的本性。從生物學角度來看,我們現代智人與我們的穴居女祖先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是動物,實際上是靈長類動物或許居生動物。我們有很多原始智人與我們的穴居女祖先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是動物,實際上是靈長類動物或許
同樣,以下是《紐約時報》健康部落格Well的一些讀者評論:
我們的身體經過數十萬年的進化,完美地適應了我們在這段時間裡99%的時間裡所過的生活方式——小型狩獵採集群體的生活。
我們(不管你喜不喜歡)都是溫血脊椎動物哺乳動物,也就是動物王國的一部分,而且只是在最近一眨眼的功夫,才相對擺脫了數千年來塑造這個物種的進化壓力。
這大概可以追溯到穴居人時代——女人外出採摘漿果,打掃衛生,總是忙個不停。而穴居人則冒著生命危險去獵殺劍齒虎或猛獁象,把獵物拖回家,然後癱倒在沙發上,喝著啤酒。我懂了——這很合理。
我並非暗示《魅力》雜誌或《紐約時報》的讀者已經完全指出了現代社會的困境。但我們很難擺脫這樣一種反覆出現的信念:在某個地方,以某種方式,事情出了問題。在這個擁有前所未有的環境改造能力、能夠讓沙漠開花、將洲際旅行縮短至幾個小時的時代,我們卻飽受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更不用說我們人類出現之前的祖先,從未經歷過的疾病的折磨:糖尿病、高血壓、類風濕性關節炎。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最新數據顯示,歷史上首次,當代人的預期壽命將低於他們的父母,這很可能是因為肥胖及其相關疾病正在削弱現代醫學的療效。
有些人懷念過去更簡單的生活,其實只是每一代人都會有的那種健忘症,他們往往忘了過去的美好時光其實並沒有那麼好。古羅馬人憂心忡忡,擔心年輕人對長輩們得來不易的智慧漠不關心。十六、十七世紀的一些作家和哲學家曾極力推崇“高貴的野蠻人”,他們與自然和諧共處,不破壞環境。而現在,我們卻擔心我們的孩子是“數位原住民”,他們從小就被電子產品包圍,無法靜下心來好好遛狗,總是忍不住一邊發短信一邊聽iPod。
我們不能認為人類的進化已經停止。
現代人之所以會感到與城市社會格格不入,另一個原因在於人們意識到,人類的基因不僅與羅馬人和十七世紀的歐洲人非常接近,而且與尼安德特人、霍蘭德提到的猿類祖先,以及數十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早期人類小群體也十分接近。的確,從遊牧生活到定居生活,從發展農業到居住在城鎮,再到城市,人類幾乎是在一瞬間就完成了這些轉變,並獲得了飛向月球、在實驗室培育胚胎以及在僅相當於我們靈活拇指大小的空間內存儲海量信息的能力。
鑑於近期變化之迅猛令人目不暇接,我們有理由下結論:我們並不適應現代生活。如果我們能像早期人類那樣生活,我們的健康、家庭生活,甚至精神狀態或許都會得到改善。至於「早期人類那樣生活」究竟意味著什麼,目前尚存爭議,但其前提——儘管是錯誤的——卻是一致的:我們的身心是在特定的環境下進化而來的,而我們卻在沒有給身體足夠的時間進化適應的情況下,改變了這些環境,最終釀成了現代生活的種種災難。
簡而言之,我們現在面臨的正是著名溫納-格倫基金會主席、人類學家萊斯利·艾埃洛所說的「遠古幻想」。她指的是基於有限的化石證據而建構的人類進化故事,但這個詞同樣適用於這樣一種觀點:我們的現代生活與人類的進化方式脫節,我們需要糾正這種不平衡。報紙文章、早晨電視節目、數十本書籍,以及提倡慢食或免烹飪飲食、赤腳跑步、與嬰兒同睡等各種措施的自助倡導者,都聲稱,像我們的祖先那樣生活會更自然、更健康。這種觀點的一個推論是,我們擅長那些在更新世時期必須做的事情,例如在小群體中提防作弊者,而不擅長那些我們不必做的事情,例如與素未謀面的人談判。
我完全贊成從演化的角度來檢視人類的健康和行為,而這一部分需要我們了解自身演化的環境。同時,我們也不能假定人類的演化已經停止,或認為演化只能緩慢地進行,在數十萬年的時間裡一步一步地發生。就在過去幾年裡,我們已經將適應高海拔環境的能力和對瘧疾的抵抗力添加到快速進化的人類特徵清單中,而且未來還會有更多特徵出現。我們甚至可以一次提取大量的DNA樣本,對整個基因組進行篩檢,尋找基因中快速選擇的痕跡。
認為自己是時代局外人,是咎由自取,這完全違背了我們如今對演化運作方式的理解──即速度至關重要。演化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或介於兩者之間,而理解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遠比將我們臃腫的現代人與肌肉發達、完美適應環境的祖先(無論這種形像是否準確)進行比較,更有意義,也更令人興奮。
我們適應不良的祖先
古生物幻想之所以是幻想,部分原因在於它假定我們人類,或至少是我們的原始人類祖先,在某個時期完美地適應了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將這種錯誤的進化論觀念——即生物體與環境之間達到理想的契合——也應用於其他生命形式,而不僅僅是人類。我們似乎模糊地認為,很久很久以前,當生物體從原始的粘液中誕生時,它們只是最終形態的粗略雛形,就像匆匆用木頭雕刻的玩具,或是藝術家最初繪製的肖像,眼睛和嘴巴的位置都留有空隙。然後,人們認為,動物們開始受到自然力量的影響。生活在沙漠中的動物更擅長抵禦烈日,而生活在寒冷地區的動物則進化出了皮毛、脂肪層或使用火的能力。一旦這些特徵出現並在種群中傳播開來,我們得到的就不是草圖,而是一個完全實現的有機體,一個既成事實,所有可愛的細節都已完成,解剖結構上的每一個細節都已確定。
認為我們自身與時代格格不入,這完全違背了我們如今對演化運作方式的理解。當然,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或許會讚歎竹節蟲完美地模仿枝葉繁茂的樹枝,甚至連翅膀上仿鳥糞的痕跡都栩栩如生;又或許會驚嘆於雪橇犬憑藉其血管間精妙的熱交換系統,能夠抵禦嚴寒。然而,它們都和其他生物一樣,充滿了妥協,都是臨時拼湊而成的。竹節蟲必須抵抗疾病,也要融入周圍環境;雪橇犬必須奔跑覓食,也要保持體溫。竹節蟲身上那些深色斑點所使用的色素,在昆蟲的免疫系統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而這種色素在某些部位的用途,在其他部位則無法使用。對雪橇犬來說,長腿便於奔跑,但更難抵禦寒冷,因為細長的四肢比粗壯的四肢更容易散失熱量。這些常常相互衝突的需求意味著每個系統都必然存在權衡取捨,因此每個系統或許都夠好,但幾乎不可能完美。無論是我們或其他物種,都從未與環境完美契合。相反,我們的適應更像是一條壞掉的拉鍊,有些齒對齊,有些齒張開。只不過,只有在我們不切實際的完美主義眼中,它才顯得破損──而我們的眼睛本身也因過往的經驗而顯得怪異。
即使沒有自然選擇對我們自身造成的這些妥協,我們仍然會受到進化史遺留的權衡取捨和「差不多就行」的解決方案的影響。人類的構造是基於脊椎動物的演化藍圖,其中包含一些奇特的構造,這些構造對於魚類來說或許合情合理,但對於陸生兩足動物而言卻難以理解。古生物學家尼爾舒賓指出,我們體內的「魚性」限制了人體機能和健康,因為在一種環境中產生的適應性特徵在另一種環境中卻會給我們帶來困擾。打嗝、疝氣和痔瘡都是我們從魚類祖先不完美地繼承了解剖學技術所造成的。這些問題至今仍然存在,原因有很多:僅僅是偶然而言,沒有出現不包含這些有害特徵的基因變異;或者更可能的是,改變食道來預防打嗝會給身體其他部位帶來難以接受的改變。如果某些事物目前運作良好,至少足以讓其攜帶者繁衍後代,那麼對於演化來說就足夠了。
我們承認進化是持續不斷的,但仍然難以理解,這意味著每一代都可以與前一代有微不足道的差異,而不會出現某個宇宙級的瞬間,讓青蛙或猴子低頭審視自身,宣布“好了,我完成了”。因此,我們的身體反映了一個不斷拼湊的系統,其中迴盪著魚類、果蠅、蜥蜴和老鼠的痕跡。想要更像我們的祖先,實際上只是想要更多同樣的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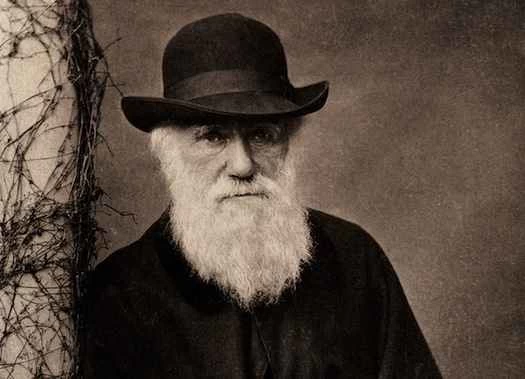
那個烏托邦是什麼時候來著?
認識到演化的連續性也清楚地表明,選擇某個特定時期作為人類和諧的標誌是徒勞無功的。為什麼我們比前人更容易感到格格不入呢?我們真的在數十萬年的時間裡保持靜止狀態,完美地適應了環境嗎?我們究竟是在過去何時達到這種適應狀態的,又是如何知道何時該停止的呢?
如果我們的穴居祖先了解演化論,他們會不會懷念雙足行走之前的日子?那時生活美好,樹木是舒適的棲身之所。人們認為,像現代鬣狗一樣從更強大的掠食者手中奪取獵物,先於或至少伴隨著人類歷史上的狩獵活動出現。那麼,那些早期的狩獵採集者是否認為,從獅子手中搶走瞪羚比自己追捕這種新奇的狩獵方式更勝一籌呢?為什麼就此止步?既然生命起源於海洋,為什麼不渴望成為水生生物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肺部仍然不適應呼吸空氣。就此而言,或許成為單細胞生物也不錯:畢竟,癌症的產生是因為我們分化的組織失控。單細胞生物不會罹癌。
人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除了有相反的證據之外,我們的祖先和我們一樣。即便我們能就一個可以追溯到的時代達成共識,但究竟這種祖先的理想狀態究竟是什麼樣的,仍然是個棘手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效法那些生活在世界少數殘存地區的現代狩獵採集者,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那麼,那些與我們(以及它們)在數百萬年前分化的祖先最為相似的類人猿呢?我們又能從化石中推斷出多少資訊?大約在20萬年前,人類在解剖學上達到了人類學家所說的「解剖學上的現代人」的標準,這意味著他們的外貌與我們大致相同,但「行為上的現代人」何時出現,以及他們究竟做了些什麼,卻遠沒有那麼清晰。因此,試圖推斷我們如今已經偏離的經典生活方式本身就帶有一定的風險。科學作家尼古拉斯·韋德在他的著作《黎明之前》中指出:“人們很容易認為,除非有相反的證據,否則我們的祖先和我們一樣。這是一個危險的假設。”
你或許會認為,狩獵採集者,或是我們幻想中的穴居人,之所以更適應環境,僅僅是因為他們在那種環境中生活了數千年——遠比我們坐在電腦前或吃著士力架的時間長得多。這在某些方面確實如此,但並非所有方面都如此。在穩定的環境中,例如深海中,持續的選擇確實能帶來更精細的適應性,因為那些不太成功的個體會被淘汰。但這種堅如磐石的穩定性在世界上實屬罕見;更新世的氣候在數千年間經歷了顯著的變化,而當人類遷徙時,即使是居住環境的微小變化,例如從溫暖到寒冷,從稀樹草原到森林,都可能帶來全新的進化挑戰。即使在完全穩定的環境中,權衡取捨也依然存在;無論你嘗試多久,你都無法既生出大腦容量大的嬰兒,又能毫無障礙地用兩條腿行走。
順便一提,有必要澄清一個誤解:現代人類生活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中,因為我們只是最近才開始擁有如今的壽命,而我們的祖先,或者說普通的狩獵採集者,只能活到三四十歲,因此從未經歷過與年齡相關的疾病。雖然人類的平均壽命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確實大幅增長,但這並不意味著幾千年前的人們在三十五歲之前都健康強壯,然後突然就去世了。
平均壽命顧名思義,是指人口中所有人口在去世前所達到的年齡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兒童因麻疹或瘧疾等疾病的死亡率很高(這在發展中國家很常見),即使沒有一個人在接近或達到40歲時去世,預期壽命也可能低於40歲。假設一個村莊有100人。如果其中一半在5歲時去世(可能是由於兒童疾病),20人在60歲時去世,剩下的30人在75歲時去世,那麼該村的平均預期壽命是37歲,但實際上沒有一個人健康地活到30歲,然後突然開始衰老。這種普遍存在的模式正是發展中國家預期壽命低得驚人的原因。並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古羅馬的人們從未經歷過老年;而是他們中很少有人能從兒童疾病中倖存下來。平均預期壽命與大多數人的死亡年齡並不相同。老化並非近期才出現的現象,但其普遍性卻是近期才出現的。
變化的速度
如果我們不從神話般的過去烏托邦中尋找前進的方向,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答案是,我們要開始提出不同的問題。與其哀嘆我們不適應現代生活,不如思考為什麼有些性狀進化迅速,有些則緩慢。我們如何了解進化的速度?如果乳糖耐受性可以在短短幾代之內在一個群體中建立起來,那麼消化和適應精製穀物的能力又如何呢?精製穀物可是原始人飲食法的禁忌。基因組學(研究生物全部基因組的學科)和其他基因技術的突破,使我們能夠確定單一基因和基因塊在自然選擇作用下改變的速度。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許多人類基因在過去幾千年裡發生了變化——從進化的角度來看,這只是眨眼之間——而另一些基因則與數百萬年來一樣,與我們遠古祖先(例如蠕蟲和酵母)的基因形式幾乎沒有變化。
如果我們把自己視為因環境與基因不匹配而受困的遺跡,就會錯過進化生物學領域一些最令人興奮的新進展。更重要的是,一個名為實驗進化的新興領域正在向我們展示,進化有時就在我們眼前發生,快速的適應可能在100代、50代,甚至十幾代或更少的時間內完成。根據生物體的壽命,這可能意味著不到一年,也可能長達四分之一世紀。在實驗室裡最容易觀察到演化,但隨著我們掌握了觀察的要點,我們也越來越多地在自然界中發現了演化的跡象。雖然人類一直在進化,但在其他類型的生物中,我們往往更容易觀察到演化過程。人類並非唯一在過去幾百年,甚至過去幾十年中,環境發生劇烈變化的物種。我和我的學生對夏威夷群島和太平洋其他地區的蟋蟀進行的一些研究表明,一種全新的性狀——使雄性蟋蟀失去鳴叫能力的翅膀突變——在短短五年內(不到二十代)就傳播開來。這相當於人類在古騰堡聖經出版到《物種起源》問世這段時間就無意識地失語了。這項以及其他類似的動物研究正在揭示哪些性狀可能在何種情況下快速進化,因為我們可以在可控的條件下即時驗證我們的想法。
過去十年,我們對這種快速演化(也稱為「生態時間尺度上的演化」)的理解有了巨大的提升。研究進化速率也具有實際意義。例如,漁民經常從溪流和河流中捕撈體型最大的鮭魚或鱒魚。魚類通常需要達到一定大小才能性成熟並具備繁殖能力,之後生長速度會減慢。與其他動物一樣,魚類在體型大小和繁殖時間之間存在權衡:如果等到體型較大再繁殖,或許可以產下更多後代,而擁有更多後代符合進化規律;但同時也存在著在繁殖之前就死亡的風險。然而,在過度捕撈導致大量魚群消失的地方,魚類的平均體型顯著縮小,因為漁民無意中選擇了更早繁殖的魚類,而進化也更青睞那些更早進行交配的魚類。問題不僅在於體型較大的魚都被捕撈殆盡,更在於魚類根本無法長到那麼大的體型。由於進化,如今負責調控性成熟時生長和體型的基因已經改變了。科學家表示,要重現幾十年前那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巨型魚,人們必須改變捕撈方式。
人們常常談論我們「本該」成為什麼樣的人,從飲食、運動到性生活和家庭,無所不談。然而,這些觀念往往有缺陷,讓我們對新食物乃至長遠來看的新想法都抱持不必要的戒心。我絕不會否認我們身體和思考中存在的進化遺產。顯然,懶惰的生活方式加上垃圾食物的飲食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但是,如果我們假設我們進化到某個特定階段後就不太可能再改變,或者將自己視為因環境與基因不匹配而受困的遺跡,那就錯過了進化生物學領域一些最激動人心的新進展。
摘自瑪琳‧祖克 (Marlene Zuk) 的著作《古幻想:進化論真正告訴我們的關於性、飲食和生活方式的信息》(Paleofantasy: What Evolution Really Tells Us About Sex, Diet, and How We Live)。版權所有 © 2013 瑪琳祖克。經出版商 WW Norton & Company, Inc. 許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