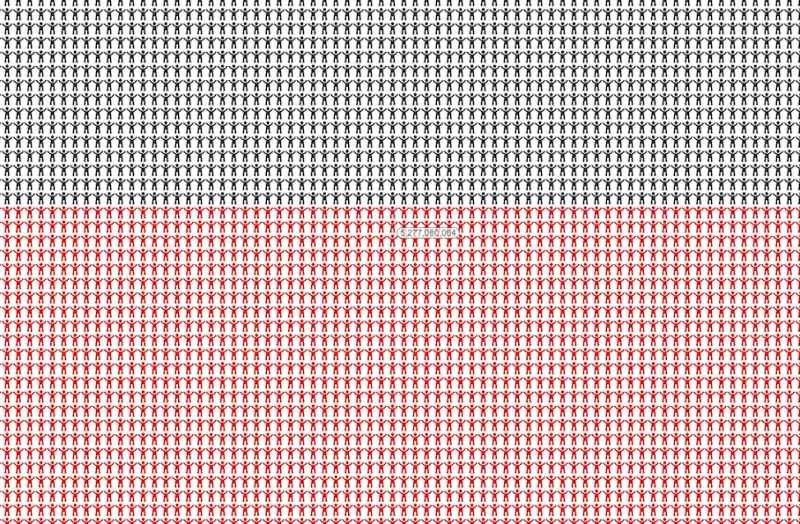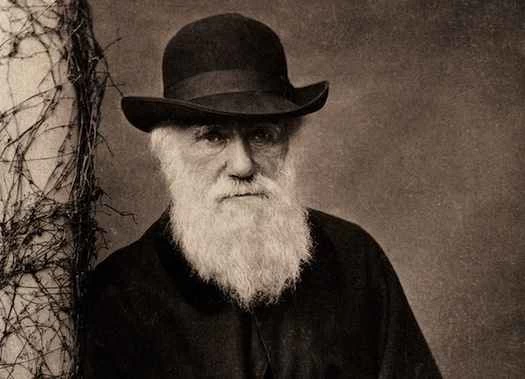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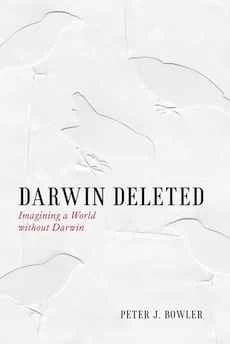
想像一下1832年12月底南大西洋一個漆黑的暴風雨之夜。在皇家海軍勘測船「貝格爾號」上,一位年輕的博物學家因暈船而踉蹌地走到甲板上。一個突如其來的巨浪使船體劇烈傾斜,他被捲入海中。瞭望員高喊“有人落水!”,但波濤洶湧的大海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而風暴又太過猛烈,值班軍官不敢冒險調轉船頭。查爾斯·達爾文就這樣離開了,菲茨羅伊船長不得不寫信給遠在英國的家人,告知他們這個噩耗。他一定會告訴他們,除了個人的悲痛之外,科學界也失去了一位前途無量的年輕博物學家,他本可以成就一番偉業。但他萬萬沒想到,達爾文最偉大的成就竟是寫出了那本世紀最具爭議的著作之一—— 《物種起源》 ,一本菲茨羅伊本人也會公開譴責的著作。
如果沒有達爾文,世界會是什麼樣子?許多人認為,科學的發展軌跡大致上不會改變。他的自然選擇進化論在當時已初見端倪,是人們對自身和所處世界思考方式的必然產物。即便達爾文沒有提出這個理論,也會有其他人提出,最有可能的就是我們熟知的自然選擇「共同發現者」——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歷史的進程大致會如我們所見,只是不會出現「達爾文主義」這個標誌性術語來指涉進化論範式。但華萊士的理論版本與達爾文的並不相同,他對理論的意義也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由於華萊士的理論構思於1858年,任何與達爾文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相媲美的著作,都要等到數年後才會出現。十九世紀末期可能出現過進化論運動,但它會基於不同的理論基礎——這些理論實際上在我們自己的世界中進行了嘗試,並且一度被認為蓋過了達爾文的理論。
達爾文理論的影響不僅限於科學本身。
達爾文主義最終得以挽救,是因為1900年孟德爾遺傳定律的「重新發現」削弱了其他進化論的合理性,而遺傳學這門新興科學的出現也動搖了其他進化論的合理性。我懷疑,如果沒有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可能要到20世紀初才會引起大多數生物學家的注意。進化論終究會出現;科學的理論體系大致上與我們今天所擁有的相同,但其構成方式會有所不同。在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演化發育生物學必須挑戰20世紀60年代以基因為中心的簡單達爾文主義,才能建構出更複雜的典範。而在非達爾文主義的世界裡,發育模型將一直佔據主導地位,並在20世紀中期進行修正以適應自然選擇的概念。
為什麼這項研究值得關注?如果生物學最終都朝著同一個方向發展,那麼為什麼有人會關心重大發現的先後順序可能與我們實際經驗的順序不同呢?就科學本身而言,這個主題或許很學術(就其最佳意義而言),但它關乎更廣泛的問題。我們最終可能會得出類似的理論,但如果這些理論出現的時間不同,我們對它們的理解也會有所不同,而這會影響大眾對它們的態度。
種族主義和各種意識形態同樣會蓬勃發展。達爾文理論的影響當然不僅限於科學本身──它也被視為唯物論和無神論興起的重要推手。進化論冒犯了許多宗教信徒,但更令人擔憂的是,它認為變化是基於偶然變異,而這些變異最終在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被淘汰。在批評者看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啟發了一代又一代的社會思想家和意識形態家,促使他們推行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嚴苛政策。神創論者經常聲稱,達爾文直接促成了雅利安人種族優越論的產生,而這種優越論激勵了納粹企圖滅絕猶太人。顯然,批評者僅僅從所謂的科學角度挑戰達爾文主義是不夠的——他們認為達爾文主義也是不道德的,因此也是危險的。即使科學證據看似誘人,人們也不應該考慮這個理論,因為它會破壞道德和社會秩序。但是,無論證據如何,某些科學觀點是否應該被法庭排除在外?
我對探索一個沒有達爾文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的興趣,源於我希望利用歷史來駁斥「自然選擇理論啟發了各種形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說法。如果達爾文沒有寫出《物種起源》,那麼我們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社會文化發展都會發生。種族主義以及各種個人和民族鬥爭的意識形態同樣會蓬勃發展,並且會從與之競爭的非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中汲取科學依據。這並非臆測,因為現實世界中達爾文主義的反對者們曾積極支持我們大多數人現在都深惡痛絕的意識形態。科學根本無法承受那些認為科學可以啟發整個社會運動的人強加給它的重擔——恰恰相反,科學是由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所塑造的。在一個沒有達爾文的世界裡,那些恐怖的事件仍然存在,但自然選擇理論不會被其批評者視為“惡魔”,因為它出現得太晚,無法發揮重要作用。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我們文化中更廣泛的緊張局勢,而正是這些緊張局勢導致了各種意識形態以無害的達爾文為代表人物。
本文經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許可轉載自彼得·J·鮑勒所著《達爾文被刪除:想像一個沒有達爾文的世界》 。 © 2013 芝加哥大學。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