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36年,瑞士數學家萊昂哈德·歐拉以繪製一幅圖結束了普魯士柯尼斯堡市民之間的辯論。普雷格爾河將這座城市(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分為四個部分,七座橋樑連接它們。一個人能否在不重複經過同一座橋樑的情況下,走過所有七座橋樑?
歐拉首先繪製了一張地圖,地圖上所有與當前問題無關的元素——房屋、街道和咖啡館——都被剔除。然後,他將這張地圖轉化為更抽象的形式,描繪的不再是一個具體的物理空間,而是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四個區域變成了點,七座橋樑變成了線。透過將柯尼斯堡轉化為簡單的節點和邊(數學家後來將這種抽象概念稱為節點和邊),歐拉得以對該系統進行數學分析。由此,他證明了一個人不可能兩次走過同一座橋。更重要的是,他首次繪製了網路圖。
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科學家在歐拉的工作基礎上發展了圖論,而這個數學分支最終成為了網路科學的基礎。但直到1959年,匈牙利數學家保羅·埃爾德什和阿爾弗雷德·雷尼提出了複雜網絡演化的方法,網絡理論才開始逐漸形成。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科學家才開始將此理論應用於真正複雜的問題。在此之前,要取得大型資料集十分困難,處理起來更是難上加難。但隨著數據獲取變得更加便捷,處理能力也日益普及,研究人員開始將圖論應用於從蛋白質相互作用到電網運作等各個領域。
阿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是聖母大學的羅馬尼亞裔物理學家,也是這些研究人員之一。在過去的十五年中,他至少兩次改變了同行們對網路的理解。他的理論影響了工程、行銷、醫學和間諜活動等領域的重要發展。他的研究或許很快就能讓工程師、行銷人員、醫生和間諜不僅理解和預測網路行為,還能控制網路行為。
巴拉巴西的研究或許很快就能讓我們不僅理解和預測網路行為,還能控製網路行為。不過,巴拉巴西最初和歐拉一樣,主要關注的是複雜系統的繪製。他尤其對埃爾德什-雷尼模型感興趣,該模型認為複雜網路是隨機的,如果網路規模足夠大,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個節點與其他節點的連結數量將大致相同。 1998年,巴拉巴西和他在聖母大學的學生們發現了一個機會,可以利用一個非常大的資料集來研究理論的適用性:聖母大學網站網域上的32.5萬個網頁。他們統計後發現,幾乎所有網頁的連結數量確實大致相同。但有幾十個網頁卻有所不同,它們的入站連結數量超過了1000個。當時,Google的PageRank演算法已經利用了這個特性來產生更相關的搜尋結果,但對於網路理論家來說,這個概念是顛覆性的,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網路本身。巴拉巴西後來寫道:“我們瞥見了網絡內部一種新的、意想不到的秩序,這種秩序展現出一種不尋常的美感和連貫性。”
面對埃爾德什-雷尼模型與自身研究結果之間的矛盾,巴拉巴西繪製了其他幾個大型複雜系統的網絡圖,包括計算機晶片上晶體管之間的連接以及好萊塢演員之間的合作。在每一種情況下,高度連結的節點(他稱之為樞紐)都是網路的決定性特徵,這不僅是一種異常現象,更是工程系統和自然系統共同遵循的組織原則。巴拉巴西與他的學生雷卡·阿爾伯特一起,對埃爾德什-雷尼模型進行了更新,使其能夠反映現實世界網絡中樞紐的存在。透過這項工作,他為科學家創造了一種工具,使他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繪製和探索各種複雜系統。
巴拉巴西關於樞紐的論文很快就發展成為樞紐本身,並成為網路科學領域被引用最多的論文之一。他將其改編成暢銷書《連結》(Linked),後來在東北大學擁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也開始借鏡樞紐理論。癌症研究人員利用它來更好地理解蛋白質網絡如何抑制體內腫瘤。在巴拉巴西的幫助下,生物學家利用它來確定抗藥性細菌代謝網絡中的抗生素標靶;這項研究可能為藥物發現開闢一條全新的途徑。巴拉巴西說,甚至有跡象表明,情報部門正在利用他的研究成果繪製恐怖分子網路圖。 「這只是措辭問題,」他說,「有很多細微的跡象表明他們正在使用它。」但是,將他的見解轉化為應用並沒有讓巴拉巴西長期保持興趣。他是一位理論家,而不是應用科學家。他說,一旦他能夠繪製出一個系統,他面臨的下一個挑戰就是預測它的行為。
2006年,巴拉巴西獲得了預測研究的機會。那一年,一個男人打電話給他,提出了一個不尋常的提議。對方自稱代表歐洲行動電話聯盟(他堅持不透露聯盟名稱),並表示掌握大量引人入勝的數據:超過六百萬用戶的匿名記錄。如果巴拉巴西同意挖掘這些數據,找出用戶更換營運商的原因,他也可以將其用於自己的學術研究。
巴拉巴西接受了這項提議。透過研究通話記錄中的模式以及每個號碼的支付詳情,他和他的實驗室成員確實建立了一種演算法,可以識別可能更換營運商的客戶。然而,在分析數據的過程中,他還發現演算法能夠識別用戶撥打電話時連接的手機訊號塔,這使他能夠推斷出通話者的實際位置。
幾個世紀以來,物理學家一直在預測粒子和行星的運動,但他們從未成功預測人們的行蹤。東北大學的巴拉巴西和物理學家宋朝明假設,如果將通話者視為粒子,他們就可以預測一個人在任何給定時間的位置。他們編寫了軟體來繪製5萬名通話者的移動軌跡。每個基地台都成為一個節點。當使用者從一個節點移動到另一個節點時,路徑就會用一條邊標記出來。然後,他們計算出每個人的熵值,熵值衡量系統中的隨機性或不確定性程度。透過將移動數據與熵值結合,巴拉巴西和宋朝明發現,他們可以在一平方英里的範圍內,以高達93%的準確率預測一個人的位置。即使是那些經常在常規活動範圍之外移動的人,其位置的可預測性也至少達到80%。
研究人員才剛開始將巴拉巴西和宋的研究成果應用於實際場景。流行病學家利用航空旅行數據來預測疾病在城市間的傳播。巴拉巴西和宋的研究成果或許能讓他們更精準地定位到單一街區。預測人們的出行方式、時間和地點,可以幫助交通工程師找到緩解交通擁堵的方法,也能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規劃者設計出能夠容納大量外來務工人員的城市。 2009年,巴拉巴西和幾位學生利用預測演算法解釋了為什麼手機病毒目前並不普遍,但一旦有足夠的手機使用相同作業系統,就可能構成嚴重威脅。
預測科學並非全然沒有弊端。巴拉巴西發表論文後,收到了大量電子郵件,指責他為「老大哥」式監控打開了方便之門。當局可以利用他的演算法,結合手機收集的GPS數據,以驚人的精度追蹤和預測公民的行踪。如果人們能夠預測系統內的行為,他們是否也能找到控制系統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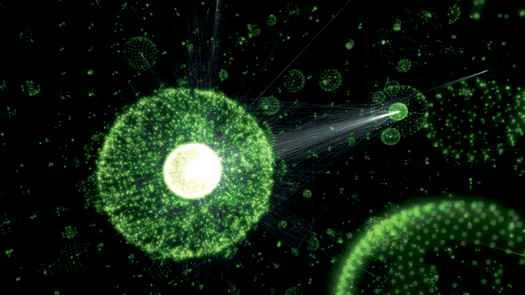
2009年,巴拉巴西到明尼蘇達大學做報告時,控制問題一直是他關注的焦點。講座前不久,他和一位工程師聊了起來。 「五分鐘後,我完全明白他根本不知道我是做什麼的,」巴拉巴西說。 “於是我問他:’你是做什麼的?’他回答說:’我是控制理論家。’”
工程師運用控制理論來預測系統對各種輸入的反應,這反過來又幫助他們製造出能接住棒球的機器人、能輕鬆轉彎的汽車以及不會墜落的飛機。巴拉巴西以前從未聽說過控制理論,於是他的新朋友帶他到白板前,畫出了基本方程式。巴拉巴西注意到這些方程式與他用來繪製網路圖的方程式非常相似,於是決定將它們應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與預測類似,控制也需要將物件視為一個系統,其中各個節點的重要性各不相同。例如,一輛車:「它由5000個部件組成,」巴拉巴西說道,「但作為駕駛員,你只能控制三到五個節點」——方向盤、油門踏板、煞車,或許還有離合器和換檔桿。 「透過這三到五個旋鈕,你可以讓這套系統行駛到汽車能去的任何地方。」他想知道的是,他是否能夠觀察任何網路(而不僅僅是人工建造的網路),並找到這些控制節點。在細胞內運作的數千種蛋白質中,他能否找到方向盤、油門踏板和煞車?
在細胞中成千上萬個運作的蛋白質中,巴拉巴西能否找到方向盤、油門和煞車?他請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劉陽宇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控制理論家讓-雅克·斯洛廷幫忙,在網路中定位「控制節點」。控制節點接收來自網路外部的指令或訊號(例如,踩下油門),並將其傳遞給網路內部的節點(例如,燃油噴射系統)。為了找到這些控制節點,劉陽宇借鑒了埃爾德什和雷尼五十年前開發的演算法,該演算法模擬訊號在網路中傳播。它從一個節點出發,沿著一條隨機邊到達另一個節點,到達該節點後,它會「擦除」除入口邊和出口邊之外的所有其他邊。該演算法反覆遍歷整個網絡,直到找到到達系統中每個節點所需的最小起始點集合。控制這些起始點,就能控制整個網路。
該團隊在37個不同的網路上測試了該演算法,其中包括監獄人口中的各種聯盟網路、酵母的代謝途徑以及包括Slashdot和Epinions在內的多個網路社群。他們發現,網路密度越高、互連性越強,其人均控制節點數量往往越少。例如,備受關注的線蟲秀麗隱桿線蟲的大腦,由297個神經元組成,卻只有49個控制節點。在酵母細胞中運作的基因網絡會產生4441種蛋白質,但Barabási發現,要控制整個系統,他需要控制其中80%的蛋白質,也就是3500個。
這聽起來像是數量太多,難以實際應用,就像一輛有3500個方向盤的車。但巴拉巴西指出兩點:雖然秀麗隱桿線蟲的神經元圖譜已經完成,但科學家目前只確定了酵母細胞基因網路中約5%的連結。科學家輸入模型的資料越多,他們就能越精確地繪製出網路中的連接圖,從而減少作業系統所需的控制節點數量。 「我們知道這些圖譜並不完整,」巴拉巴西說,「但它們每天都在變得更加完善。」他也表示,他的理論適用於對網路的完全控制。如果科學家想要進行部分控制——例如,在細胞內誘導特定蛋白質的表達——他們只需要掌握少得多的節點。
與巴拉巴西的大多數研究一樣,這項研究需要時間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找到控制點是一回事,而真正對特定網路(無論是Facebook還是人類免疫系統)施加影響,則是完全不同的挑戰。
首批突破很可能出現在醫學領域。透過辨識細胞生長系統中的控制節點,科學家可以將成熟細胞逆轉回胚胎狀態,從而創造出新的幹細胞來源。 “有些疾病的根本原因在於失控,”巴拉巴西說,“如果能夠在細胞或神經元層面控制這些失控因素,或許就能治愈這種疾病。”
當然,控制既可以用於善,也可以用於惡。行銷人員可能會學會如何更好地操縱消費者,政府也可能發展出新的手段來壓制民眾。巴拉巴西說,我們有責任界定控制應該如何運用,以及不該如何運用。 「我們必須認識到,控制是理解過程的自然發展,」他說。 「但控制關乎意志,而意志可以透過法律來控制。我們必須作為一個社會共同努力,弄清楚我們能將控制推向何種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