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萊恩·克里斯蒂安的新書《最像人類的人》(The Most Human Human)現已推出平裝版,講述了作者——一位擁有計算機科學和哲學學位的年輕詩人——如何為了贏得圖靈測試的“最像人類的人”獎而努力的故事。這項測試旨在衡量人類智慧與人工智慧的優劣。在準備向評審團(透過匿名電傳打字機介面)證明自己並非機器的過程中,本書對思考的本質進行了深刻而嚴謹的探討。我們是否應該著眼於與機器在分析和邏輯方面的優勢競爭,而不是培養我們自身的人類優勢,從而注定失敗?
圖靈測試試圖辨別電腦究竟是「像我們一樣」還是「不像我們」:人類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自身在萬物中的位置。而計算機在二十世紀的發展,或許標誌著這種位置的首次改變。
圖靈測試的故事,以及人們對人工智慧的種種猜想、熱情和不安,其實就是我們對自身的種種猜想、熱情和不安的故事。我們擁有哪些能力?我們擅長什麼?是什麼讓我們與眾不同?因此,回顧電腦科技的發展史,只是了解全貌的一半。另一半則是人類對自身的思考史。
[...]
半球沙文主義:電腦與生物
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說:“神經病學和神經心理學的整個歷史都可以看作是左半球研究的歷史。”
右腦,或一直被稱為「次要」的大腦半球,長期以來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雖然很容易證明左側大腦不同部位損傷的影響,但右腦相應的症狀卻遠不那麼明顯。人們通常輕蔑地認為右腦比左腦更“原始”,而左腦則被視為人類進化的結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觀點是正確的:左腦更加複雜和專門化,是靈長類動物,尤其是人類大腦發展後期才出現的產物。另一方面,正是右腦控制所有生物為了生存所必需的、辨識現實的關鍵能力。
左半球就像一台附加在基本生物大腦上的計算機,是為程序和圖式而設計的;而古典神經學更關注圖式而不是現實,因此,當一些右半球綜合徵最終出現時,它們被認為是怪異的。
神經學家VS Ramachandran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左腦不僅負責實際發出語音,也負責建構語言的句法結構,以及大部分所謂的語意──也就是對意義的理解。而右腦則不負責口語,它似乎更關注語言中一些微妙的方面,例如隱喻、寓言和歧義的細微差別——這些技能在小學教育中往往被忽視,但它們對於透過詩歌、神話和戲劇推動文明進步至關重要。我們傾向於稱左腦為主要或「主導」半球,因為它就像一個沙文主義者,包辦了所有的發言(或許也包括大部分的內在思考),自詡為人類最高特質-語言——的寶庫。
“不幸的是,”他解釋說,“沉默的右腦無法進行任何抗議。”
略微偏向一側
藝術與教育專家(兼爵士)肯·羅賓遜爵士表示,這種對左腦的奇怪關注和「主導」在幾乎所有世界教育體系的學科等級制度中都顯而易見:
在教育體系中,數學和語言位居頂端,人文學科緊跟在後,藝術墊底。這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是如此。而且幾乎在所有教育體系中,藝術內部也存在著等級。藝術和音樂在學校裡的地位通常高於戲劇和舞蹈。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教育體系像教數學一樣每天教孩子跳舞。為什麼?為什麼不呢?我認為這非常重要。我認為數學固然重要,但舞蹈也同樣重要。如果允許的話,孩子們會一直跳舞;我們所有人都會。我們都有身體,不是嗎?我錯過了什麼會議嗎?事實上,隨著孩子長大,我們開始從腰部以上逐步地教育他們。然後我們才開始注意他們的頭部。而且往往是偏向一側。
當然,這一方指的是左派。
羅賓遜指出,美國教育體系「宣揚了一種極度狹隘的智力和能力觀念」。如果像薩克斯所說的那樣,左腦“就像一台加裝在基本生物大腦上的電腦”,那麼,當我們認同左腦的活動,並以此為傲,將自身“定位”於左腦之中時,我們實際上就開始把自己視為電腦。透過更好地教育左腦,更好地重視、獎勵和培養牠的能力,我們實際上已經開始變成電腦了。
[...]
以自己為中心
正如薩克斯所說,我們是被電腦附加在生物體上的。重點不在於貶低其中任何一方,就像雙體船不應該變成獨木舟一樣。重點也不在於我們憑藉理性擺脫了半獸性,並試圖憑藉意志力更進一步。關鍵在於這種張力。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於合作、對話、二重奏。
文字遊戲“Scattergories”和“Boggle”玩法不同,但計分方式相同。玩家各自列出自己想到的單詞,然後比較彼此的列表,劃掉出現在多個列表中的單字。表格上剩餘單字最多的玩家獲勝。我一直覺得這種計分方式有點殘酷。想像一下,一個玩家想出了四個單詞,而她的四個對手每人只想到了一個。這一輪打成平局,但感覺卻並非如此……隨著人類獨特性的界限不斷縮小,我們把承載自身身份認同的“雞蛋”放在越來越少的籃子裡;然後電腦出現,拿走了最後一個籃子,劃掉了最後一個單詞。這時我們才意識到,獨特性本身從來都無關緊要。我們為了將其他物種和其他機制拒之門外而建造的壁壘,也同樣將自己困在了裡面。而電腦打破了這最後一扇門,讓我們重見光明。
誰能想到,電腦最早的成就竟然是在邏輯分析領域──這種能力被認為是使我們與地球上所有生物最顯著的差異?誰能想到,它在學會騎自行車之前就能駕駛汽車和引導飛彈?誰能想到,它在學會閒聊之前就能創作出巴赫風格的、聽起來像樣的前奏曲?誰能想到,它在學會釋義之前就能進行翻譯?誰能想到,它在看到椅子後,像任何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一樣說出“椅子”這個詞之前,就能寫出半真半假的後現代理論文章?
我們常常忘記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物是什麼。電腦正在提醒我們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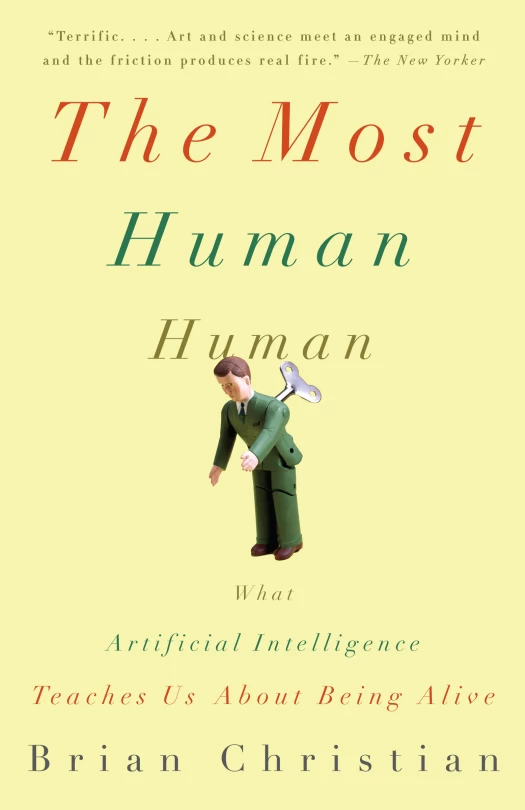
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高中時是咖啡師:她每天都要對濃縮咖啡進行無數次細微的調整,從咖啡豆的新鮮度到機器的溫度,再到氣壓對蒸汽量的影響,無一不考慮在內。同時,她也像章魚一樣靈巧地操作機器,並和形形色色的顧客就各種話題閒聊。後來她上了大學,找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枯燥乏味的資料輸入。她無比懷念當咖啡師的日子──那份工作才真正需要她動腦筋。
我認為,對分析思維的怪異迷戀,以及隨之而來的對生命中生物性——也就是動物性——和具身性的貶低,是我們最好摒棄的。或許,在人工智慧時代的開端,經過幾代「稍微偏離中心」的生活之後,我們終於開始重新找回自我中心。
此外,我們都知道,在資本主義勞動市場和前資本主義勞動力教育體系中,專業化和差異化至關重要。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2005年出版的《藍海戰略:如何創造無人競爭的市場空間並使競爭變得無關緊要》,其核心思想是避開競爭激烈的“紅海”,奔向未知的市場領域——“藍海”。在一個只有人類和動物的世界裡,我們或許可以傾向左腦思考。但計算機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切。最藍的海域已不再是過去的樣子。
此外,人類對「沒有靈魂」的動物的蔑視,以及不願承認自己是其他「野獸」的後代,如今在各個方面都有所減弱:世俗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興起,對自身以外的生物的認知和行為能力的日益重視,以及(並非巧合的是)一種比任何普通黑猩猩或倭黑猩猩都更加沒有靈魂的生物的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甚至可能成為動物權利的福音派。
事實上,我們很可能已經見證了左腦偏向的巔峰時期。我認為,回歸到對大腦、思考以及人類身分更平衡的觀點是一件好事,它會帶來各種複雜任務的全新視角。
我認為,只有體驗和理解真正脫離肉體的認知,只有看到那種真正與感官現實脫節、純粹抽象的事物的冷漠、死寂和疏離,才能使我們擺脫這種狀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我們回歸感官。
我的研究生導師之一,詩人理查德·肯尼(Richard Kenney),將詩歌描述為“一種混雜的藝術——歌唱式的語言”,他將這種藝術比作地衣:一種實際上並非生物體,而是真菌和藻類共生體的一種形式,這種共生體如此普遍,以至於它本身看起來就像一個物種。 1867年,當瑞士植物學家西蒙·施文德納(Simon Schwendener)首次提出地衣實際上是兩種生物體時,歐洲頂尖的地衣學家們都嘲笑他——其中包括芬蘭植物學家威廉·尼蘭德(William Nylander),他甚至戲稱地衣為“stultitia Schwendeneriana”,這是偽植物學傻瓜,這是一種偽植物學傻瓜,這是施文德納文德納。當然,施文德納的觀點完全正確。地衣確實是一種讓人產生親緣關係的奇特“物種”,但這種感覺卻又十分貼切。
吸引我的是這個概念——混雜的藝術、地衣、猴子和機器人手牽手——它似乎也描述了人類的生存狀態。我們的本質本身就是一種混雜。我意識到,一些最美好、最人性化的情感,正是源於這種電腦/生物互動的地衣狀態,源於慾望與理性交融的河口,源於一個足夠清醒地認識到自身局限並不斷挑戰極限的系統:好奇、著迷、啟迪、驚奇、敬畏。
拉馬錢德蘭:「我曾接診過一位病人——一位來自紐約的神經科醫生——六十歲時突然開始出現癲癇發作,病灶位於他的右側顳葉。癲癇發作當然令人擔憂,但令他驚訝和欣喜的是,他生平第一次對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事實上,他開始用詩歌的語言思考,創作出大量的詩開始給他的靈感,他開始用一個新的詩意思考,創作出大量的詩?
人工智慧很可能就是這樣一種癲癇發作。
摘自布萊恩克里斯蒂安所著《最有人情味的人》(The Most Human Human),版權所有 © 2011 布萊恩克里斯蒂安。經蘭登書屋旗下Anchor出版社許可摘錄。保留所有權利。未經出版商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或轉載本摘錄的任何部分。
從亞馬遜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