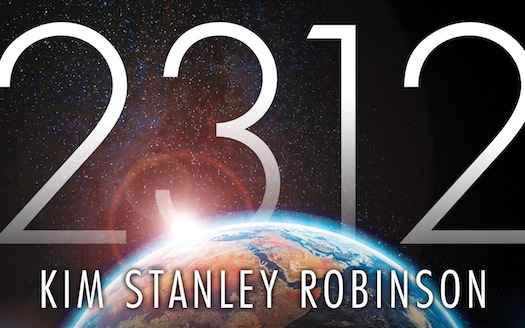
序幕
太陽總是即將升起。水星自轉如此緩慢,以至於你可以在它崎嶇的表面上快速行走,趕在黎明之前到達;許多人正是這樣做的。許多人甚至以此為生。他們大致向西行進,始終走在壯麗白晝的前面。有些人匆匆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停下來查看他們之前接種了生物浸出金屬植物的縫隙,迅速刮掉任何積聚的金、鎢或鈾的殘留物。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是為了瞥見太陽的身影。
水星古老的面貌飽經風霜,凹凸不平,以至於它的晨昏線——黎明破曉的區域——呈現出一片寬闊的黑白明暗交錯的景象:炭黑色的凹陷處點綴著耀眼的白色高地,這些高地不斷擴展,直至整顆星球都像熔融的玻璃般明亮,漫長的白晝由此開始。這片日影交錯的區域通常寬達三十公里,即使在平坦的平原上,地平線也只有幾公里之遙。然而,水星上幾乎沒有平坦的地形。所有古老的撞擊痕跡依然存在,還有一些長長的懸崖,是這顆星球最初冷卻收縮時留下的。在這片起伏的土地上,光線可以突然躍過東方的地平線,向西飛躍,照射到遠處的某個高地上。每個行走在水星上的人都必須注意這種可能性,了解太陽照射時間最長的地點和時間——以及如果碰巧遇到強光,可以躲到哪裡避暑。
或者他們是故意停留的。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會在漫步途中,在某些懸崖和火山口邊緣駐足,這些地方往往有佛塔、石堆、岩畫、因紐特石堆、鏡子、牆壁和金石碑等標記。日行者們就站在這些地方,面向東方,靜靜等待。
他們凝視的地平線是黑色岩石之上的漆黑空間。陽光撞擊岩石形成的超薄霓虹氬氣大氣層,只透著黎明前最微弱的光芒。但日行者們知道時間,所以他們等待著,凝視著——直到——地平線上閃過一道橙色的火焰海豚,他們的血液瞬間沸騰。隨後,更多短暫的光芒出現,向上掠過,劃出一道道弧線,斷裂後在空中自由飄蕩。星辰啊星辰,即將閃耀在他們面前!他們的面罩已經變暗並偏光,以保護他們的眼睛。
橙色的光暈從最初出現的位置向左右兩側擴散,彷彿地平線上燃起的火焰正向南北蔓延。隨後,太陽光球層(即太陽的實際表面)的一部分閃爍片刻,然後停留片刻,緩緩向兩側溢出。根據配戴的濾鏡不同,太陽的實際表面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形態,從藍色的漩渦到橙色的脈動光團,再到簡單的白色圓圈。向左右兩側溢出的光暈不斷擴散,遠超想像,直到你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正站在一顆恆星旁的鵝卵石上。
是時候轉身逃跑了!但當一些日行者設法掙脫束縛時,他們卻驚慌失措——絆倒在地——爬起來,驚慌失措地向西狂奔。
在此之前——最後再看一眼水星上的日出。在紫外線下,它呈現出永恆的藍色漩渦,溫度越來越高。當光球層的圓盤被遮蔽後,日冕的奇妙舞動便更加清晰可見:所有磁化的弧光和短路,以及燃燒的氫氣團塊在夜空中傾瀉而出。或者,你也可以遮擋住日冕,只觀察太陽的光球層,甚至可以放大圖像,直到對流單元燃燒的頂端顯露出來,成千上萬個蜿蜒曲折的對流單元,每一個都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火雲,它們每秒燃燒五百萬噸氫氣——按照這個速度,這顆恆星還能燃燒。所有這些細長的火焰針狀物圍繞著太陽黑子——燃燒風暴中不斷移動的漩渦——呈現圓形圖案舞動。大量的針狀物匯聚在一起,如同被潮水沖刷的海藻床。所有這些錯綜複雜的運動都有非生物學的解釋——不同的氣體以不同的速度運動,磁場不斷變化,塑造著無盡的火焰漩渦——這一切都只是物理學,僅此而已——但事實上,它看起來栩栩如生,比許多生物都更有活力。在水星黎明的末日景像中凝視著它,你根本無法相信它不是活的。它在你的耳邊咆哮,它與你對話。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日行者都會嘗試各種不同的觀測濾鏡,然後根據自身情況做出選擇。特定的濾鏡或濾鏡組合會成為一種崇拜形式,一種個人或集體的儀式。人們很容易沉迷於這些儀式中;當日行者站在各自的觀測點上觀看時,信徒們常常會被眼前景像中的某些東西所吸引,一些前所未見的圖案,一些脈動和流動中某種令人神魂顛倒的東西;突然間,熾熱纖毛的嘶嘶聲變得清晰可聞,一種湍急的咆哮——那是你自己的血液咆哮。於是,人們停留的時間太長。有些人視網膜被灼傷;有些人失明;還有一些人被當場殺死,被不堪重負的太空衣出賣。有些人甚至十幾人或更多人一起被烤熟。
你覺得他們一定是傻瓜嗎?你認為自己永遠不會犯這樣的錯誤嗎?別這麼肯定。你根本無法想像。這景像你從未見過。你或許認為自己已經麻木,即便你如此博學多識,除了頭腦之外的一切都無法再引起你的興趣。但你錯了。你是太陽的創造物。近距離觀賞太陽,它的美麗與威嚴足以使任何人神魂顛倒,進入一種恍惚的狀態。有人說,這就像看到了上帝的真容。的確,太陽為太陽系中所有生物提供能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就是我們的神。它的景象足以讓你的思緒徹底消散。人們正是為此而追尋它。
所以,我們有理由擔心斯旺·爾·洪,她比大多數人更熱衷於嘗試新鮮事物。她經常去曬太陽,而且總是遊走在危險的邊緣,有時甚至在陽光下停留太久。巨大的雅各天梯,顆粒狀的脈動,流動的針狀物……她已經愛上了太陽。她崇拜太陽;她在房間裡供奉太陽神索爾·因維克圖斯,每天早上醒來都會舉行普拉塔薩姆迪亞儀式,向太陽致敬。她的許多景觀藝術和行為藝術作品都與太陽有關,如今,她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土地和身體上創作戈爾茲沃斯和阿布拉莫維奇式的作品。所以,太陽是她藝術的一部分。
如今,這也成了她的慰藉,因為她正獨自在外悲傷。如果有人站在終結者城那高聳的黎明之牆頂端的長廊上,就能在南方的地平線附近看到她。她必須抓緊時間。這座城市正沿著軌道滑行,穿過赫西俄德和庫拉薩瓦之間一個巨大的凹陷底部,陽光很快就會傾瀉而下,照耀西方。史旺必須在陽光照射之前趕進城,但她仍然站在那裡。從黎明之牆頂端看去,她就像一個銀色的玩具。她的太空衣配有一個巨大的透明圓形頭盔。她的靴子看起來很大,沾滿了黑色的灰塵。她就像一隻穿著靴子的小銀蟻,站在那裡悲傷,而她本來應該匆匆趕回城西的登船平台。其他的日行者已經匆匆趕回城裡了。有些人拉著小車或有輪子的拖車,運送他們的補給,甚至是他們的同伴。他們精心安排了回程時間,因為這座城市的運作規律非常可預測。它無法偏離既定的時間表;黎明的到來使鐵軌膨脹,而城市的底盤則緊緊包裹著鐵軌;因此,陽光驅使著這座城市向西移動。
隨著城市臨近,歸來的日行者們蜂擁而至,湧上裝卸平台。有些人已經外出數週,甚至數月,才能完成一趟完整的環城之旅。當城市緩緩駛過時,它的大門將會打開,他們將徑直走進去。
那件事很快就要發生了,斯旺也應該在那裡。然而她仍然站在她的岬角上。她不只一次需要視網膜修復手術,也常常被迫像兔子一樣奔跑,否則就會喪命。現在,這一切又要重演了。她正位於城市的正南方,被水平的光線完全照亮,就像視野中一道銀色的瑕疵。人們忍不住對這種魯莽的行為大聲斥責,儘管這毫無用處。 “斯旺,你這個傻瓜!亞歷克斯已經死了——一切都無法挽回了!快逃命吧!”
然後她真的這麼做了。生命戰勝死亡──求生的渴望──她轉身飛翔。水星的重力幾乎與火星完全相同,常被稱為速度的完美重力,因為習慣了這種重力的人可以以巨大的跳躍橫跨陸地,一邊揮舞手臂保持平衡一邊飛奔。斯旺就是這樣跳躍、揮舞手臂——有一次被一隻靴子絆倒,臉朝下摔在地上——然後她又跳起來,再次向前躍去。她必須在城市還在旁邊的時候到達平台;下一個平台在十公里外的西邊。
她走到月台樓梯前,抓住扶手,縱身躍上,從月台邊緣縱身躍入半閉的船閘中。
史旺和亞歷克斯
當史旺步履蹣跚地走上終結者大廈中央的宏偉階梯時,亞歷克斯的追悼會開始了。全城的居民都湧上林蔭大道和廣場,默默地肅立著。城裡也來了不少訪客;一場由亞歷克斯召集的會議原本即將召開。上週五,她還熱情地接待了他們;而下週五,他們卻要為她舉行葬禮。她突然倒下,他們沒能救活她。如今,城裡的居民,來訪的外交官:所有亞歷克斯的親人,都在悲傷之中。
斯旺在黎明牆半山腰停了下來,再也爬不上去了。她腳下是屋頂、露台、陽台。巨大的陶瓷盆子裡種著檸檬樹。一條蜿蜒的斜坡,像個小小的馬賽,兩旁是白色的四層公寓大樓,黑色鐵欄桿的陽台,寬闊的林蔭大道和狹窄的小巷,一直延伸到俯瞰公園的步道。這裡人頭攢動,彷彿在她眼前不斷分化,每張臉都鮮明地展現自己的個性,同時也代表著某種類型──奧爾梅克球體、斧頭、鐵鍬。欄桿上站著三個矮人,每個大約一公尺高,都穿著黑色衣服。樓梯腳下聚集著剛到的日行者,他們看起來皮膚黝黑,滿身塵土。看到他們,斯旺感到一陣刺痛──就連日行者也是為了這一刻而來。
她轉身走下樓梯,獨自漫步。聽到消息的那一刻,她便衝出城市,奔向荒野,只為獨處。如今,她無法忍受在亞歷克斯的骨灰撒放儀式上被看見,也不想在那一刻見到亞歷克斯的伴侶姆卡雷特。於是,她來到公園,融入人群。所有人都靜靜地站著,抬頭仰望,神情悲痛欲絕。他們互相扶持著。有那麼多人依賴亞歷克斯。他是水星之獅,是城市的心臟,是系統的靈魂。是那個幫助過你、保護過你的人。
有些人認出了斯旺,但他們沒有打擾她;這比任何慰問都更讓她感動,她淚流滿面,不停地用手指擦拭著臉頰。這時,有人攔住了她:“你是斯旺二紅?亞歷克斯是你的祖母嗎?”
「她是我的一切。」斯旺轉身離開。她覺得農場可能比較空曠,於是離開了公園,穿過樹林向前走。城市廣播裡正播放著葬禮進行曲。灌木叢下,一隻鹿正用鼻子拱著落葉。
她還沒走到農場,黎明之牆的大門就打開了,陽光穿透穹頂下的空氣,投射出兩道常見的黃色半透明光束。她凝視著光束中的漩渦,那是大門開啟時揚起的滑石粉,彩色的細小顆粒隨著上升氣流飄散開來。這時,一個氣球從牆下的高台上升起,向西飄去,氣球下的小吊籃搖曳著:是亞歷克斯;怎麼會這樣?音樂中一股強烈的反抗之聲從低音區湧出。當氣球進入其中一道黃色光束時,吊籃「噗」的一聲爆裂開來,亞歷克斯的骨灰飄落下來,脫離光束,進入城市的天空,隨著下落漸漸消失,如同沙漠中的雨幡。公園裡傳來一陣歡呼,那是掌聲。幾個年輕人在某個地方短暫地高喊著:「艾莉克斯!艾莉克斯!艾莉克斯!」掌聲持續了幾分鐘,逐漸匯成一陣悠長的節奏。人們不願放棄,彷彿那一刻就意味著結束,他們就要失去她。最終,他們還是放棄了,延續著後艾莉克斯時代的人生。
她必須上去和亞歷克斯一家會合。想到這兒,她不禁呻吟一聲,在農場裡漫無目的地遊蕩。最後,她僵硬地、茫然地走上大樓梯,中途停下來,喃喃自語:「不,不,不。」但這一切都毫無意義。她突然意識到:現在做什麼都無濟於事。她想知道這種狀態會持續多久——似乎會永遠持續下去,一陣恐懼襲來。究竟是什麼才能改變這一切?
最終,她振作起來,走向黎明牆上的私人紀念碑。她必須向所有與亞歷克斯關係最親近的人問好,給姆卡雷特一個短暫而粗暴的擁抱,還要忍受他臉上的神情。但她看得出來,他並不在家。這不像他,但她完全理解他為何會離開。事實上,看到他離開讓她感到如釋重負。想到自己當時的心情有多糟糕,再想想姆卡雷特與亞歷克斯的關係比她親密得多,他陪伴亞歷克斯的時間又比她長得多——他們曾是多年的伙伴——她無法想像他離開會是什麼感覺。或許她能想像。所以現在,姆卡雷特凝視著另一個世界,彷彿從另一個世界凝視著她——彷彿在向她表達某種敬意。這樣她才能擁抱他,承諾稍後會去看他,然後去黎明牆最高的露台上與其他人交流,之後再走到欄桿邊,俯瞰這座城市,透過那透明的穹頂,眺望外面漆黑的夜空。她們正穿過柯伊伯帶,她向右望去,看到了廣重隕石坑。很久以前,她曾帶亞歷克斯到那裡,在廣重隕石坑的邊緣,幫她完成一件「黃金級」作品——一個仿照日本藝術家廣重最著名畫作之一的石浪。為了平衡那塊構成浪峰的石頭,她們嘗試了無數次,但都以失敗告終。和亞歷克斯一樣,斯旺總是笑得肚子痛。現在,她看到了那道石浪,它還在那裡──從城市裡就能勉強看見。然而,構成浪峰的石頭已經不見了──或許是被經過的城市震動撞倒的,或許是被陽光照射的。又或許是聽到消息後倒下的。
幾天后,她去姆卡雷特的實驗室拜訪了他。他是這個系統中頂尖的合成生物學家之一,實驗室裡擺滿了各種機器、罐子、燒瓶,還有螢幕上密密麻麻地顯示著複雜多變的彩色圖表——生命以其龐大而復雜的形態,一鹼基對一鹼基對地構建而成。他們在這裡從零開始創造了生命;他們建構了許多如今正在改變金星、土衛六、海衛一——甚至整個宇宙的細菌。
現在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姆卡雷特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目光空洞地望著牆壁,什麼也沒看見。
他起身抬頭看著她。 “哦,斯旺——見到你真高興。謝謝你過來。”
“沒關係。你怎麼樣?”
“不太好。你呢?”
「糟透了,」斯旺坦白道,感到內疚;她最不想做的就是給姆卡雷特增加負擔。但這種時候撒謊毫無意義。他只是點了點頭,心不在焉地想著自己的事。她看出他心不在焉。他桌上的立方體裡裝著蛋白質的模擬影像,鮮豔的假彩色顏料糾纏在一起,根本無法理清。他一直在努力工作。
「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她說。
“是啊,嗯。”
一陣沉默後,她問道:“你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嗎?”
他迅速搖了搖頭,彷彿這件事無關緊要。 “她一百九十一歲了。”
我知道,但是…
“那又怎樣?我們終究會崩潰,斯旺。遲早有一天,我們會崩潰。”
“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
“不,沒有為什麼。”
“或者,那又該如何呢……”
他再次搖了搖頭。 「什麼都有可能。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可能是大腦關鍵部位的動脈瘤。但病因有很多種。最神奇的是我們首先能夠活下來。”
斯旺坐在桌邊。 “我知道。但是,那麼……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工作。”
“但你剛才明明說……”
他從洞穴裡探出頭看了她一眼。 「我沒說沒用。那樣說不對。首先,我和亞歷克斯在一起七十年了。我們相遇時我已經一百三十歲了。所以,這很重要。而且,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很有意思,就像一個謎題。一個非常大的謎題。實際上,太大了。」說著說著,他停了下來,一時說不下去。斯旺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雙手摀住臉。斯旺坐在他身邊,一言不發。他用力揉了揉眼睛,握住她的手。
「死亡是無法戰勝的,」他最後說。 “它太大了。它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說到底,就是熱力學第二定律。我們只能希望能夠延緩它,把它推遲。這應該就足夠了。我不知道為什麼還不夠。”
“因為那樣只會讓情況更糟!”斯旺抱怨道,“活得越久,情況就越糟!”
他搖了搖頭,又擦了擦眼睛。 「我覺得不對。」他長長地嘆了口氣。 「總是很糟糕。不過,真正感受到痛苦的是那些活著的人,所以……」他聳了聳肩。 「我想你的意思是,現在看來好像是某種錯誤。有人死了,我們就會問為什麼。難道就沒有辦法阻止這一切嗎?有時候確實有。但是……”
「這肯定是個錯誤!」斯旺宣稱。 「現實犯了個錯誤,現在你們在糾正它!」她指著螢幕和立方體。 “對吧?”
他又哭又笑。 “對!”他抽泣著擦了擦臉說,“真是愚蠢。太狂妄了。我是說,妄圖改變現實。”
「但這很好,」斯旺說。 “你知道的。它讓你和亞歷克斯相伴七十年。而且它還能打發時間。”
「沒錯。」他長嘆一口氣,抬頭看著她。
“但是——沒有她,一切都將不一樣了。”
斯旺感覺到這殘酷的真相如潮水般湧來,讓她無比絕望。艾利克斯曾是她的朋友、保護者、老師、繼祖母、代理母親,她扮演著所有這些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她也是她歡笑的源泉,快樂的源泉。如今,她的離去帶來了一種冰冷的感覺,一種扼殺所有情感的力量,只留下空虛的絕望。純粹的麻木。這就是我。這就是現實。無人能夠逃脫。不能繼續下去,卻又必須繼續下去;她們永遠也無法超越那一刻。
於是他們繼續前進。
實驗室外門傳來敲門聲。 「進來,」姆卡雷特語氣略顯生硬地喊道。
門開了,門口站著一個身材矮小、容貌姣好、上了年紀的女子——她身材苗條,留著整齊的金色馬尾辮,穿著一件休閒的藍色夾克——身高大約到斯旺或姆卡雷特的腰部,像長尾猴或狨猴一樣仰望著她們。
「你好,讓,」姆卡雷特說。 「斯旺,這位是來自小行星帶的讓·熱內特,他來這裡參加會議。讓是亞歷克斯的好朋友,也是聯盟的調查員,所以他有一些問題想問我們。我說過你可能會過來看看。”
小傢伙朝斯旺點了點頭,手撫胸口。 「我對你的損失深表哀悼。我來不僅是為了表達哀悼,也是想告訴你,我們很多人都很擔心,因為艾利克斯是我們一些最重要項目的核心成員,她的去世太突然了。我們希望確保這些項目能夠繼續進行,坦白說,我們中的一些人很想知道她的死因是否是自然死亡。」
「我向瓊保證確實如此,」姆卡雷特看到斯旺臉上的表情後說道。
珍妮特似乎不完全相信這種保證。 「亞歷克斯有沒有跟你提過敵人、威脅——或任何危險?」小女孩問斯旺。
“不,”斯旺努力回憶著說,“她不是那種人。我的意思是,她總是非常樂觀,相信事情會好起來的。”
“我知道,確實如此。但正因如此,如果她說過任何與她一貫樂觀態度不符的話,你才會記得。”
“不,我不記得有這樣的事。”
她有沒有留給你遺囑、信託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資訊?或留言?
如果她過世了,有什麼需要打開的嗎?
“不。”
“我們確實設立了一個信託,”姆卡雷特搖著頭說,“裡面沒有什麼不尋常的東西。”
“請問我可以參觀她的書房嗎?”
艾莉克斯的書房設在姆卡雷特實驗室最裡面的一間房間裡,現在姆卡雷特點點頭,領著這位小督察沿著走廊朝那間房間走去。史旺跟在她們身後,驚訝於珍妮特竟然知道艾莉克斯的書房,驚訝於姆卡雷特這麼快就帶她去看,也驚訝於這種「敵人」、「自然死亡」及其隱含的反義詞。艾莉克斯的死,居然是由某個警察之類的人來調查?她簡直無法理解。
當珍妮特坐在門口,努力理解這一切意味著什麼,試圖接受這個事實時,她正對亞歷克斯的辦公室進行徹底搜查,打開抽屜,下載文件,用一根粗大的魔杖掃過每一處表面和物品。姆卡雷特面無表情地看著這一切。
小督察終於完成了檢查,他站在斯旺面前,好奇地打量她。斯旺坐在地上,兩人視線差不多齊平。督察似乎還想問什麼,但最後還是沒說出口。最後,他說:“如果你想起什麼可能對我有幫助的事情,請告訴我。”
「當然,」斯旺不安地說。
督察隨後向他們道謝並離開了。
「那是怎麼回事?」斯旺問姆卡雷特。
「我不知道,」姆卡雷特說。斯旺看出他也很沮喪。 「我知道亞歷克斯參與了很多事情。她從一開始就是蒙德拉貢聯盟的領導人之一,而他們有很多敵人。我知道她一直擔心一些系統問題,但她沒有告訴我任何細節。」他指了指實驗室。 「她知道我不會那麼感興趣。」他做了個痛苦的表情。 “她知道我有自己的問題要處理。我們很少談論工作。”
「但是——」斯旺開口,卻不知該如何繼續。 “我是說——敵人?亞歷克斯?”
姆卡雷特嘆了口氣。 “我不知道。在某些事情上,利害關係可能很大。你知道,蒙德拉貢家族也有反對勢力。”
“但是,仍然…”
“我知道。”停頓片刻後,她又問:“她給你留下什麼了嗎?”
“不!她為什麼要死?我的意思是,她又沒料到自己會死。”
“很少有人會這樣。但如果她擔心保密問題,或者某些信息的安全,我能理解她為什麼會覺得你能成為她的避風港。”
“你是什麼意思?”
“那麼,她難道不能在不告訴你的情況下往你的立方體裡放點東西嗎?”
「不,寶琳是個封閉系統。」斯旺敲了敲她的右耳後。 “這些天我基本上都把她關著。而且艾利克斯也不會這麼做。她肯定不會不先問過我就跟寶琳說話。”
姆卡雷特又嘆了口氣。 「唉,我不知道。據我所知,她也沒給我留下任何東西。我的意思是,亞歷克斯應該會瞞著我們藏起什麼東西。但什麼也沒發現。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斯旺說:“所以屍檢結果沒有任何異常嗎?”
「不!」姆卡雷特說道,但他還在思考。 “可能是先天性腦動脈瘤破裂,導致腦實質出血。這種情況時有發生。”
斯旺說:“如果有人做了什麼導致出血……你一定能分辨出來嗎?”
姆卡雷特皺著眉頭盯著她。
這時,他們聽到實驗室外門又傳來敲門聲。兩人對視一眼,彼此心頭一緊。姆卡雷特聳了聳肩;他沒想到會有人來。
「進來吧!」他又喊道。
門開了,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與熱內特探長截然相反的人:一個身材魁梧的男人。下顎突出、臀部肥大、臀部脂肪堆積、眼球突出——蟾蜍、蠑螈、青蛙——就連這些字本身都令人不快。斯旺突然想到,擬聲詞或許比人們意識到的更為普遍,他們的語言如同鳥鳴般迴盪著世界的迴響。斯旺腦海中閃過一絲奇思妙想。蟾蜍。她曾在亞馬遜雨林見過一隻蟾蜍,它棲息在池塘邊,濕漉漉的、長滿疣子的皮膚泛著青銅色和金色的光澤。她很喜歡它的樣子。
“啊,”姆卡雷特說道,“瓦赫拉姆。歡迎來到我們的實驗室。斯旺,這位是來自泰坦星的菲茨·瓦赫拉姆。他是艾利克斯最親密的同事之一,也是她最喜歡的人之一。”
史旺有些驚訝,亞歷克斯的人生竟然會有這樣的人,而她卻毫不知情,她皺著眉頭看著那個男人。
瓦赫拉姆微微低頭,像個自閉症患者似的鞠躬。他把手放在胸口,用一種青蛙般的沙啞聲音說道:“我很抱歉。艾利克斯對我,對我們很多人來說,都意義非凡。我愛她,在我們一起工作的過程中,她是至關重要的人物,是領導者。我不知道沒有她我們該怎麼辦。想到我現在的感受,我都難以體會你們的感受。”
「謝謝,」姆卡雷特說。人們在這種時候說的話真奇怪。斯旺一句也說不出來。
艾利克斯曾經喜歡過一個人。斯旺輕拍右耳後的皮膚,啟動了她因受罰而關閉的魔術方塊。現在,寶琳會透過斯旺右耳邊傳來的輕柔聲音告訴她一切。斯旺最近對寶琳很不耐煩,但突然間,她又想知道些什麼。
Mqaret問道:“那麼會議將會如何發展呢?”
“大家完全同意推遲會議並重新安排時間。現在誰也沒有心情再開會了。我們會解散,之後再重新聚會,可能是在灶神星上。”
啊,沒錯:沒有亞歷克斯,水星就不再是聚會場所了。姆卡雷特對此點了點頭,並不感到意外。 “所以你將返回土星。”
“是的。但在我離開之前,我很想知道亞歷克斯是否給我留下什麼。任何形式的信息或資料都可以。”
姆卡雷特和斯旺交換了一個眼神。 「不,」他們異口同聲地說。
姆卡雷特做了個手勢。 “傑內特警督剛才問過我們這個問題。”
「啊。」蟾蜍人瞪大了眼睛看著他們。這時,姆卡雷特的一個助手走進房間,請求他的幫助。姆卡雷特找了個藉口離開,然後斯旺就獨自面對來訪者和他的問題。
這個蟾蜍人個頭很大:肩膀寬闊,胸膛寬闊,肚子也很大。腿卻很短。人們都很奇怪。他搖了搖頭,用一種低沉沙啞的聲音說道——她不得不承認,這聲音很美——雖然有點像青蛙叫,但卻很放鬆,低沉渾厚,音色飽滿,有點像巴鬆管或低音薩克斯管——“很抱歉在這個時候打擾您。真希望我們能在其他情況下相遇。
斯旺對此感到驚訝。在裡爾克的紀念碑前,她豎起了一圈哥貝克力T形石碑,儘管它們取材自一萬多年前的古物,但看起來卻非常現代。 「謝謝,」她說。看來她真是一隻有教養的蟾蜍。 “告訴我,你為什麼覺得亞歷克斯可能會給你留言?”
「我們之前一起做過一些事,」他閃爍其詞地說,目光躲閃著。她看出他不想談這件事。但他還是來問的。 「而且,她總是對你讚不絕口。很明顯你們倆關係很親密。所以……她不喜歡把東西存在雲端或任何電子文件裡——真的,她不喜歡用任何媒介記錄我們的活動。她更喜歡口耳相傳。」
「我知道,」斯旺說著,感到一陣刺痛。她彷彿聽到亞歷克斯說:我們得談談!這是一個虛偽的世界!她那雙湛藍的眼睛,她的笑聲,全都消失了。
那個高大的男人看出了她的變化,伸出了手。 「我很抱歉,」他再次說道。
「我知道,」斯旺說。然後:“謝謝。”
她坐在姆卡雷特的一張椅子上,努力讓自己想一些別的事。
過了一會兒,那個大個子用低沉而溫和的聲音說道:“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斯旺聳了聳肩。 “我不知道。我想我還是再到水面上去看看吧。那是我……讓我重新振作起來的地方。”
“你能給我看看嗎?”
「什麼?」斯旺說。
「如果您能帶我去那裡,我將不勝感激。或許可以帶我參觀一下您的某個裝置作品。或者,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注意到這座城市正在接近丁托列托火山口。我的航天飛機還要過幾天才起飛,我很想去那裡參觀博物館。我有一些問題在地球上無法解答。”
“關於丁托列託的問題?”
“是的。”
「嗯……」斯旺猶豫了一下,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不失為一種消磨時間的方式,」那人建議。
「是的。」這番話讓她有些惱火,但另一方面,她其實一直在尋找一些事情來分散注意力,一些事後可以做的事情,卻一直沒找到。 “好吧,我想也是。”
“非常感謝。”
列表(1)
易卜生和伊姆霍特普;馬勒、馬蒂斯;紫式部、彌爾頓、馬克吐溫;
荷馬和霍爾拜因,觸碰邊緣;
奧維德的作品在篇幅更大的普希金作品的邊緣熠熠生輝;
戈雅與索福克勒斯風格重疊。
梵谷與塞萬提斯、狄更斯、史特拉汶斯基和維亞薩、利西波斯、埃奎亞諾(一位西非奴隸作家,住在不靠近赤道的地方)在一起。
蕭邦和瓦格納的作品並排擺放,尺寸相同。
契訶夫和米開朗基羅都創作過雙環形山。
莎士比亞和貝多芬,巨大的水池。
Al-Jāi,Al-Akhal。阿里斯托克斯努斯,阿什瓦戈沙。黑澤明、魯迅、馬致遠。普魯斯特和珀塞爾。梭羅和李白,魯米和雪萊,斯諾里和皮加勒。瓦爾米基、惠特曼。布勒哲爾和艾夫斯。霍桑和梅爾維爾。
據說,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的命名委員會在一次年會上喝得酩酊大醉,拿出最近收到的第一批水星照片的馬賽克圖,把它當作飛鏢靶,互相喊出著名畫家、雕塑家、作曲家、作家的名字——給飛鏢命名,然後把它們扔向地圖。
有一個名為 Pourquoi Pas 的懸崖。
